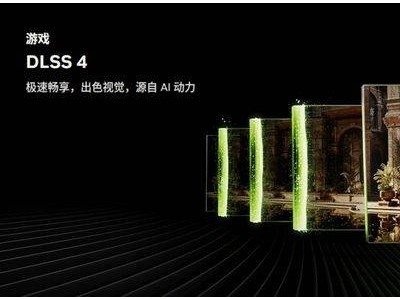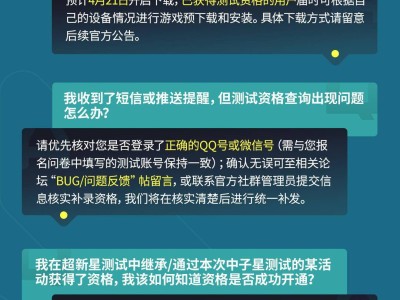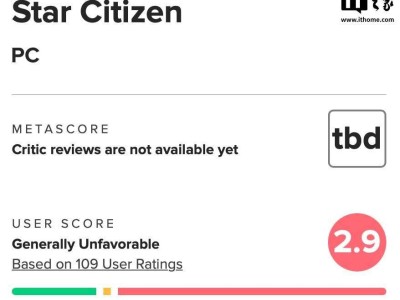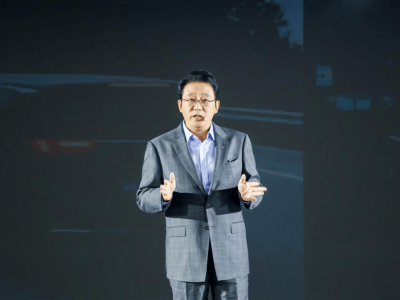近年来,美国顶尖学府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校园内,一股令人忧虑的趋势逐渐显现:来自全美收入前1%家庭的“超级精英”子女数量,已悄然超越来自后50%家庭学生的总和。这一数据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优绩主义(Meritocracy)承诺的深刻反思——这一曾以“能力至上”为旗号的理念,旨在打破贵族世袭的枷锁,为所有人铺设公平竞争的阶梯。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优绩主义非但未兑现平等的理想,反而催生出更为隐蔽的阶层固化现象。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其著作《精英陷阱》中,尖锐地指出这一问题的本质。他回顾道,优绩主义最初作为一场进步运动兴起,推翻了旧贵族“血脉决定命运”的垄断,以考试分数与职业成就作为社会流动的标尺。彼时,精英阶层凭借能力与勤奋脱颖而出,似乎完美契合了“公平竞争”的叙事。

然而,当这一代精英成为父母后,他们以惊人的资源投入子女教育,从私立中小学到量身定制的SAT辅导、科研项目与全球游学,富裕家庭通过天价教育投资,将子女送入顶级私校和常春藤盟校。马科维茨指出,如今常春藤盟校新生中,通过SAT考试达到名校录取线的寒门学子,数量远不及精英阶层子女。
更令人讽刺的是,这场竞争中的“赢家”同样深陷困局。优绩主义将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捆绑,迫使精英以超负荷工作维系优越感。一位年薪数百万美元的投行高管,甘愿为额外收入牺牲全部生活;斯坦福毕业生在硅谷昼夜编码,只为证明自己配得上“天才”标签。这种自我剥削的背后,是优绩主义对自我价值的扭曲,当工作成为衡量尊严的唯一尺度,休息与热爱皆被异化为“懒惰”的罪证。
普通人的处境更为残酷,他们不仅被剥夺了上升通道,更被优绩主义的道德叙事宣判“失败源于不够努力”。马科维茨警告称:“系统远比个人强大。”优绩主义已演变为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通过教育筛选、职场竞争与文化驯化,将所有人卷入一场没有出口的无限游戏。
在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的议题上,马科维茨与Edu指南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他强调,优绩主义最初旨在推动机会平等,如今却成为障碍,因为在新的竞争中,对教育进行巨大投资成为孩子成功的唯一途径,而这只有富有的父母才能负担得起。
马科维茨指出,名校的选拔正在成为富裕家庭的选拔。在美国,公立学校每年为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约为1万至1.5万美元,而最精英的私立学校则可能高达6万至7万美元。这些私立学校中,约80%的孩子来自收入前5%的家庭。这些最富有的孩子,在学业上投入最多,当他们申请大学时,自然拥有最好的考试成绩和水平。
对于招生录取过程中偏向于富裕家庭学生的现象,马科维茨表示,系统根据考试成绩和成绩进行评估,而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在于拥有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因此,对财富的偏向贯穿于优绩主义之中,尽管并非直接,但影响深远。
当被问及是否有其他标准或方法帮助不那么富裕家庭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时,马科维茨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他认为,精英大学和学校需要招收更多的学生,变得不那么精英化。通过增加入学人数,创造更多机会供精英以外的人进入,这将使学校本身不那么排外。
马科维茨还指出,优绩主义不仅在经济上伤害人们,剥夺普通人获得好工作和高工资的机会,还在道德上侮辱人们,认为人们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够聪明、努力或道德高尚。这种观念导致人们在个人层面失败时,倾向于责怪自己,而非整个系统。
马科维茨强调,即使是精英本身也深陷困局。他们过度工作以证明优越性,放弃了自由和时间,以换取对他们没有实质性好处的金钱。这种生活模式导致精英们筋疲力尽、变形,甚至自我异化。同时,富裕的孩子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必须做被告知的事情的观念,缺乏自由。
在谈到AI技术对未来教育投资的影响时,马科维茨认为,AI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某些受过教育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新技术主要取代了中等技能的工作,对高技能工作只是作为补充。因此,技术取代了一些中产的工作,但也让精英变得更好。然而,AI也将开始争夺一些精英工作,如医生和律师的某些职责。
最后,马科维茨提醒人们,无论身处系统的哪个位置,系统都非常强大。因此,不要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结果而赞扬或责怪自己,这很大程度上与系统有关。同时,当能够抓住一点自由时,要去做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别人控制的奖赏。